GRAZIA红秀中文网:日本高清视频wwww色-福柯逝世40周年|米歇尔·福柯:政治经济学与自由主义
在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中,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一个重要转型期。简单地说,这位哲学家的兴趣从规训配置(dispositifs disciplinaires)转向了主体诠释学(herméneutique du sujet)和对自我的关注,从臣服(assujettissement)转向了自由践行。然而,在《认知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1976)与《快感的享用》(L'use des plaisirs,1984)两本著作出版期内,福柯没有出版过其他著作。因此,他在法兰西公学院的演讲非常有用。尽管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福柯没有出版这些演讲稿,甚至在遗嘱中明确表示他不希望这些演讲稿在死后出版,但这些演讲稿还是帮助我们了解了他不断发展的思想。我们只能对不愿出版的原因加以猜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讲座只是某种探索。《安全、领土、人口》(以下简称《STP》)和《生命政治的诞生》(以下简称《NBP》)构成了一个始终在探索自身的项目,这有时会导致作者做出许多重新安排,开拓许多并不可靠的路径,甚至产生矛盾,从而难以连贯地理解整体。

福柯
《安全、领土、人口》与《生命政治的诞生》这两部作品的目的是要写一部“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的历史。我们将不再赘述这一漫长而宏伟的谱系,而是借此机会介绍一些在他未来的思想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概念:治理、引导、自由、牧领权(pouvoir pastoral)。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就在我们眼前发展起来。文章从福柯式的经典问题切入:18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和控制机制,其基础是福柯所说的安全机制。之后转入另一个问题,加以补充,抑或取代前一个问题,该问题即对经济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影响的反思。关注焦点的改变以及福柯通过政治经济学对自由主义的建构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政治经济学与自由主义
在这两本书中,福柯研究了治理概念的谱系。在他看来,最有趣的时刻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当时出现了安全机制,在历史层面上替代了司法—法律机制(mécanisme juridico-légal)和规训机制(mécanisme disciplinaire)。
为了解释什么是安全机制(mécanismes de sécurité),福柯研究了治理粮食短缺所采取的政策。18世纪中叶的重大转变在于,饥荒从此被视为一种自然现象。福柯主要考察的对象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路易·保罗—阿贝耶(Louis-Paul Abeille),他在《一位商人关于谷物贸易性质的书信》(Lettre d'un négociant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des grains,1763)中解释了如何分析粮食短缺问题。他认为,我们必须拒绝任何道德批判,因为这涉及到的是一种自然机制。这也不是一个通过调控来防止时而丰裕时而匮乏的问题,因为要使这一现象消失,必须先让它发生。正是通过深入“这一现实的根本要素”,才能限制、进而消灭匮乏。因此,问题在于将安全机制与现实连接起来,甚至需要取消谷物管理,鼓励价格上涨,因为通货膨胀会带来双重效果,既吸引外来商人,也会鼓励农民扩大作物种植面积。正是通过顺其自然,才能实现自行抑制(autofreinage)。规训机制规定了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而安全机制则是以退为进,掌握正在发生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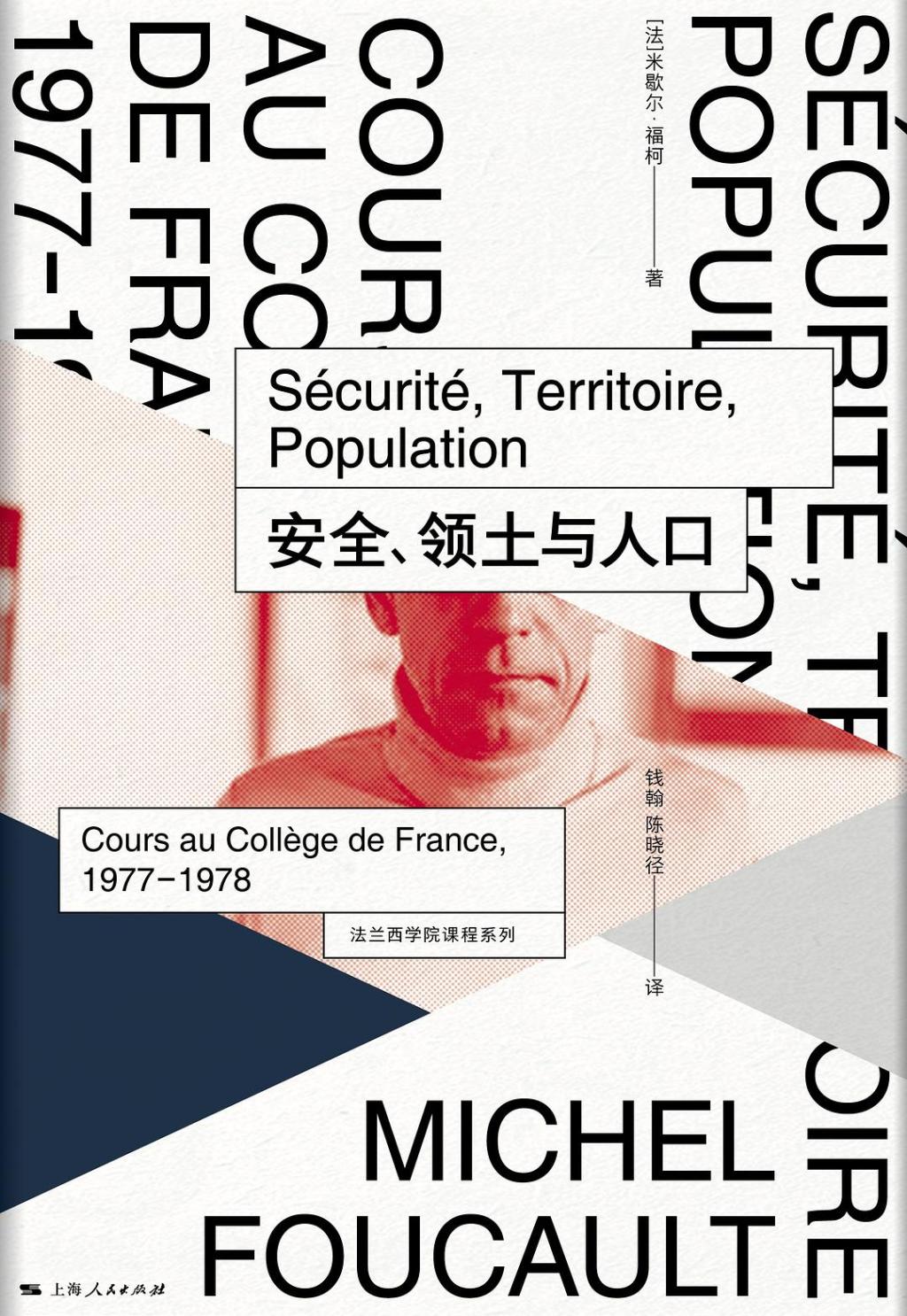
《安全、领土、人口》中译本
为证明这类机制的普遍性,福柯将同时期兴起的天花疫苗接种与治理粮食短缺措施,相提并论。他认为,疫苗接种的目的也不是通过建立规训体制(systèmes disciplinaires),禁止病人与病人之间的一切接触来预防疾病,而是恰恰相反,其手段是激活疾病,使人能够发展出消除疾病的手段。其核心思想是,各种现象通过因果循环进行自我调节。
安全机制的出现带来了一场普遍的变革,因为它涉及到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甚至是生物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催生它的思想工具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在当时正作为一门自命的学科出现。福柯在多处谨慎地强调,这一发明只是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权力技术变革的一个方面。然而,政治经济学在福柯的著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是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可以被定义为理性的行为科学(science du comportement rationnel,将稀缺资源分配给其他目的)。但我们所有的行为不都是理性的吗?因此,它成为了安全机制(dispositif de sécurité)的原型,同时也是对启蒙运动后西方社会中权力的组织和分配进行高度反思的模板。
从重商主义,跨越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最后到最现代的自由主义,这位哲学家反复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地位,但奇怪的是这一点却被福柯的评论者所忽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普遍性的忽视?可能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并没有那么吸引福柯,因此它的存在定会淡去。不过,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却令人惊讶。福柯为何如此强调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出乎意料,因而更值得一提。事实上,福柯以一种非常协调的方式发展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史观,将之作为治理理性(raison gouvernementale)转型的思想工具。
政治经济学与治理的自我限制
限制政府行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18世纪下半叶。诚然,由于行政君主制(monarchie administrative)的发展,这是一个官僚活动不断扩大的时代,其行动手段和职权范围都大大扩展。其中的引领者(artisans)往往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如莫勒帕(Maurepas)、特鲁丹(Trudaine)和杜尔阁(Turgot)。托克维尔则将法国大革命解释为行政集权加剧的结果。越来越独立、报复心也越来越强的公共舆论不断批评政府的这种行为,以对之加以限制,而这种行为往往会被视为绝对主义的表现。
尽管这些启蒙运动的争论也涉及经济议题,但核心问题是政治自由主义。然而,福柯对政治自由主义并不感兴趣,他只关注政府的自我限制(autolimitation gouvernementale),对这个问题,他有时甚至近乎痴迷。对政治自由主义而言,权力只有在自身之外才能找到限制自己的原则。现在,这种外在于治理理性的限制,无论是源于宗教、法律还是政治,都不涉及这两门课程的问题。“内部限制意味着我们不是在……某些事物中寻找这种限制的原则,例如,不是从上帝为所有人规定的自然权利中寻找,也不是在启示的经文中寻找,更不是着眼于特定时刻同意加入社会的主体意愿。这种限制的原则不应在外在于治理的因素,而应在治理实践的内部因素中寻找”(《生命政治的诞生》,13页)。
排除了政治后,这种寻求政府自我限制的做法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将法律搁置在一边,这一点贯穿了两卷书的始终。这种排除对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直接的益处,因为政治经济学经常被视为与法律完全相悖的形象(figure antinomique du droit)。然而,对法律的批评并不是说它外在于治理理性,更不是说它在强制遵守限制其行动范围的法律规则或原则方面的能力太弱。福柯在晚期的反思(1979年3月28日的课程,倒数第二章)中专门讨论了“经济人"(homo œconomicus)和“看不见的手”(main invisible),他将契约理论产生的法律主体与政治经济学想象的利益主体进行了对比。他强调了两者在一个他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存在区别:契约理论产生的法律主体需要放弃某些权利以保护他人,而政治经济学想象的利益主体却从未被要求违背自己的利益。相反,正如冉森主义者尼科尔(Pierre Nicole)以及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所表明的那样,每个人都必须追求自己的利益,可以说是培养和强化自己的利益,这样才能使经济繁荣发展。福柯总结道:“市场和契约的功能恰恰相反”(《生命政治的诞生》,279页)。这种显著的差异正是政治经济学吸引福柯的第二个原因:政治经济学所证明的政府自我限制的必然结果是,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利益的绝对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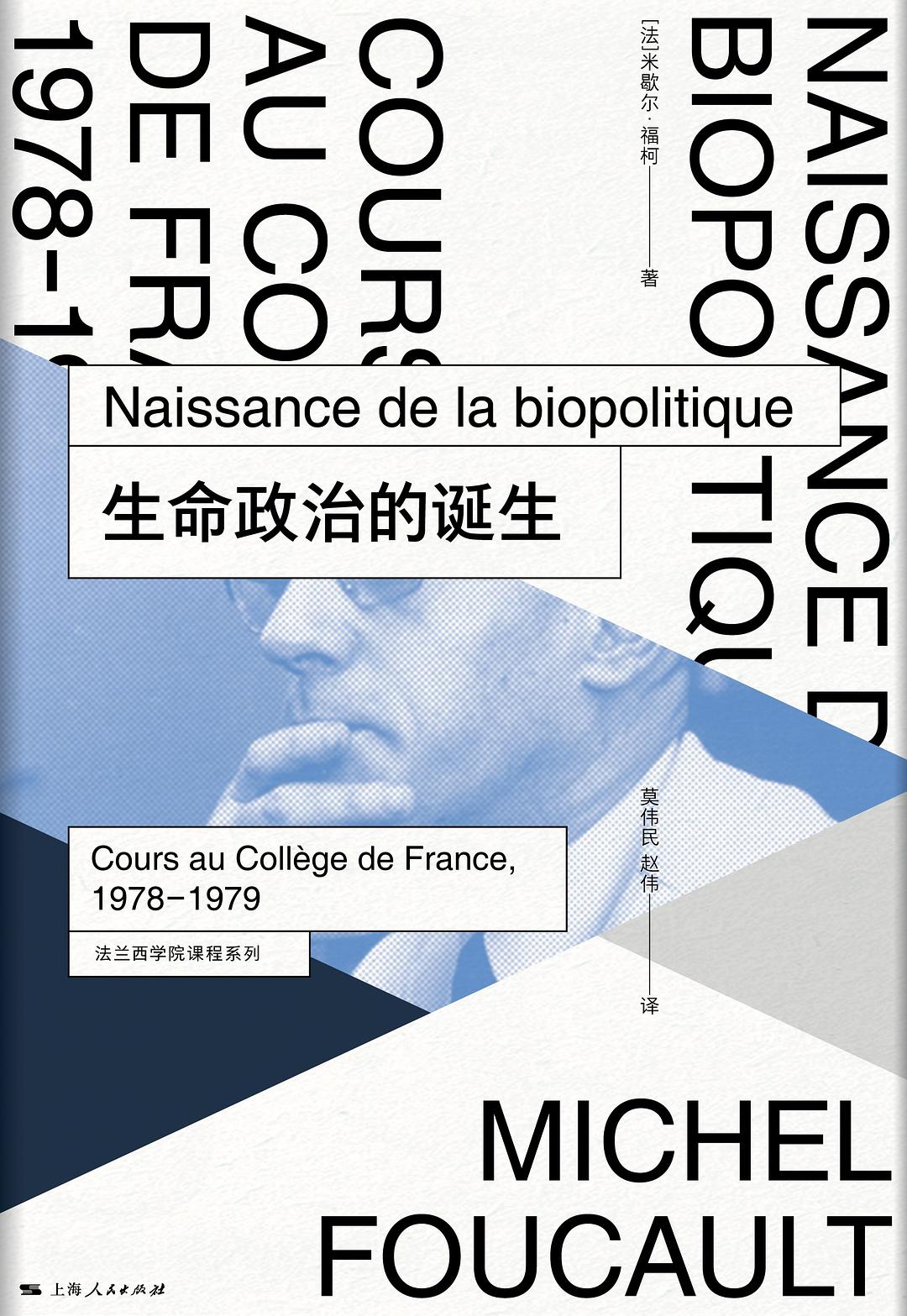
《生命政治的诞生》中译本
这种二律背反的构建(construction antinomique)导致法律和政治经济学以两种完全不相容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其后果之一就是不可能有一门经济—法律科学(science économico-juridique),而这门科学的不存在正体现了这种对立。政治—法律世界与经济世界的绝对异质性对福柯的研究方法至关重要,他也有意坚持这一点: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方式强化了政治经济学的独特地位,而政治经济学是唯一能够迫使治理限制自身的理性话语。
这种对法律的忽视是有代价的。它导致财产权被排除在外,而在福柯思想中完全没有财产权这一概念。原因显而易见,因为财产权是作者不感兴趣的外部限制之一。它甚至是为保护个人免受国王专横之害而提供的首批保障之一。十六世纪末的许多主权问题思想家,当然首先是让·博丹,还有十七世纪上半叶的绝对君主制理论家,如卡丹·勒布雷特(Cardin Le Bret),都以对私有财产的无形尊重为名,质疑国王在未经人民代表同意的情况下征收新税的权力。但财产权的缺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18世纪的自由主义作家本身就将财产权置于他们理论分析的核心位置,使尊重财产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原则和存在的理由。
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和自然主义
福柯现在的问题是:一旦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合理性,即私有财产,那么政治经济学又该如何立足?答案就在于无处不在的“自然”(nature)和“自然主义”(naturalisme)这两个概念。如果权力无需对行为加以干预,那是因为它是自然的,这赋予了它自主性和合理性。
福柯如何看待这种“自然”的历史发展?对社会和经济现象的自然性的认识可以追溯到15世纪80年代和16世纪50年代之间的大转型,当时“人们心向自然,后者不再容忍任何政府”(《安全、领土、人口》,243页)。这一重要判断的含义如下。在这一转型之前,君主将神圣的主权延伸至大地之上。福柯在此引用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对他而言,君主的治理与主权的行使并无特殊性:统治(régner)与治理(gouverner)是两件相同或不可分割的事情。如果有这种连续性,那是因为君主是“从上帝到家庭之父,经过自然和牧首的伟大连续体”的一部分。正是这一连续性在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中叶之间被打破,而古典认识论正是在这一时期创立的。当然,这种与科学革命在时间上的巧合并非偶然。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所表明的是,上帝通过普遍规律(lois générales)来管理世界,而这些规律一旦确立,就不可改变。换句话说,上帝不是以一种牧首的方式(mode pastoral)(即个人化的方式(mode individualisé))管理世界,而是通过原则来统治世界。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同,但与前一个主题关系密切的新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前一个主题在政治领域的必然延伸。虽然君主不再(或不再只是)必须将神圣的主权扩展到人间,但他确实肩负着一项只有他才能完成的特殊任务,这项任务不同于君主或牧首的职能,即使他可以从中汲取灵感:此即,他必须治理国家。有了这种新的制度,我们一方面有了一种脱离治理主体、遵循原则(principia naturae)的自然,另一方面又有了一种治理艺术,它必须处理16世纪末出现的新对象,即公共事物(res publica)。这种治理技艺必须寻求一种理性,这种理性既不能在对自然的模仿中得到启发,也不能从上帝的法则中得到启发。这就是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其目的是维护国家和管理国家的日常运作。就福柯的目标而言,这种国家理性的第一个特点是,它不了解前一种意义上的民众,即由能够自主行为的经济主体组成的民众。在18世纪中叶之前,principia naturae与ratio status之间的这种对立一直占主导地位,直到18世纪中叶,两者通过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某种统一。从那时起,世界的治理建立在以自然为基础的新兴政治经济学之上。
福柯文本中的一个奇论在于他提出的政治经济学与自然之间的对应关系。经济思想史的传统解释认为,正是由于发现了物理世界的自然秩序,启蒙运动时期的经济学家才认为,同样的秩序也可以支配社会世界,而且至少从重农主义者的时代开始,他们宣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发现了社会世界的规律。福柯对这一点并不感兴趣,他抛开了政治经济学在18世纪60年代为自由主义辩护时提出的科学论据,尤其是自由市场是最有效、最公平的财富生产和分配组织这一观点。他认为,如果说经济学是一个自然问题,那是因为经济学家将个人行为描述为一个自然问题。这就是“人口”(population)概念的关键性发明,它确立了政府行为的自我限制原则。他是一个“绝对崭新”(absolument nouveau)的政治人物,与前几个世纪的法律和政治思想完全格格不入。福柯将其与“全景式监狱”(panopticon)的概念进行了对比。“全景式监狱”是君主的一个古老梦想,其目的是对人民进行详尽的、个性化的监控,而安全系统只对自然机制感兴趣。
从根本上说,人口的特征是可以被描述为自然的规律性。这些规律分为两类。首先,正如18世纪的统计学家们的惊人发现,在人口特征的变量(死亡人数、患病人数、事故的规律性等)中存在着常量、稳定或可能的比例。其次,存在着一种行为常量(invariant comportemental),这一常量使整个人口具有一种单一的驱动力:欲望(désir),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如果允许这种欲望发挥作用,就会导致与人口的总体利益相一致的结果。
这一分析引出了看待政府干预的两种不同方式,这两种方式在自由主义思想中同样存在。第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君主来说,民众是不透明的,因为一方面,决定民众的变量不仅太多,而且是自变的(autonomes),因此难以为君主所了解;另一方面,只有个人才能知道自己的愿望和利益是什么,以及实现这些愿望和利益的手段是什么。因此,任何权力都无法取代个人。更重要的是,这些具体行为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情况过于复杂,无法简单地加以解释。因此,政府的知识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一主题在18世纪下半叶经常出现,尤其是在有关谷物贸易自由的讨论中。在20世纪,哈耶克最系统地阐发了这一观点。第二种看待政府干预的方式认为,这些规律性的存在使得人口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治理技术能够加以掌握。其中一些常量和稳定的比例是可以计算的,而利益,因为它可以抑制激情——正如许多十八世纪的作家所强调的那样——是个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掌权者所理解的保证。我们将看到,这种诊断的模糊性也存在于福柯关于治理干预及其限制的思想中。
目前,我们必须强调人口概念的原创性,正如福柯在其课程第一部分中提出的那样。当然,一切出发点是政治经济学,后者无非是人口管理科学(science de la gestion des populations),即思考治理应该凭依的思想模型(modèle intellectuel)。但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政府性比“纯粹和简单的经济学说”(la pure et simple doctrine économique)具有更广泛的使命,因为它适用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经济过程相关联的许多方面。福柯的观点非常宽泛,不仅包括人口和健康,还包括“行为方式”(STP,24页),换句话说,就是与自然或自然现象有关的一切。“人口,就是这样一个延伸广阔的东西,从物种的生物学本源直到通过公众的概念所提供的可控制的外形”(STP,77页)。正因为如此,他得出结论说,政治经济学,更广义地说,自由主义,就是自然主义。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诞生于将激情和兴趣逐步限制在经济层面,即限制在追求利润和获取物质财富的层面,而福柯则通过人口概念反其道而行之,使政治经济学知识成为扩大政府性的模型。在这一阶段,其后果是对政治的排斥。
值得注意的是,福柯重新解读和诠释了18世纪作家对社会现象的重要性和自然性的这一发现,将分析引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是坚持国家对民众行使生命权力(bio-pouvoir)的概念。这是福柯研究控制个人的项目的延续,但是立场更为激进,更强调身体的生物维度(dimension biologique),自1990年代初以来,该计划调动了福柯的一部分哲学遗产。与此不同,另一方向则倾向于一种克制的自由主义(libéralisme de l'abstention),鉴于自身和民众的自主性,干预不再合适。正如第一堂课所证明的那样,福柯对这两个研究计划都很感兴趣,尽管有些时候表现得比较隐晦。但是在这两堂课中,他显然对后一个研究项目,以及对探索政治经济学的启发式效用,更有兴趣。
但他说的是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呢?福柯显然将政治经济学与小政府(moindre gouvernement)联系在一起(NBP,31页)。正因如此,他将目光聚焦于十八世纪中叶,更确切地说,是自由化敕令落实的那十年(1754—1764年),这是权力技术发生巨大变化和现代治理理性(raison gouvernementale moderne)出现的时期。当谈到作为治理型的“经济知识”(savoir économique)时,他只提到了相当有限的文本,这导致他忽视或模糊了这种知识的其他形式。例如,他很难理解谷物管理制度的合理性(STP,35页)。
这导致他将安全机制(即基于事物之实在(réalité des choses)的自由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组织形式对立起来。“安全与在想象中运作的法律不同,与在现实的补充中运作的规训不同,它试图在现实之中运作,通过一系列分析和专门机构,它使现实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STP,49页)。福柯非常重视自由主义的这一方面,自由主义的运作基础是事物发生时的实在性(réalité),是可客观化的自然现象。然而,这种对立是脆弱的,因为他的推理所依据的缺粮机制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也都是想象力作用的结果。内克(福柯从未引用过)在《谷物贸易立法》中证明了这一点,他强调了市场运作在多大程度上是集体心理的结果,这种集体心理阻碍了规律性的存在,排除了商品自然价格或正常价格的形成。
因此,福柯在泛泛提及“经济知识”的同时,以非常顺畅的方式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只保留了有助于构建和强化人口观念的内容。
有度治理(Gouvernement frugal)
很明显,人口(自然)/治理术(人为)这对组合发挥着核心作用。虽然福柯声称自己主要思考的是治理的历史,但最感兴趣的始终还是人口问题,换言之,就是社会的自主性(autonomie de la société)。但困难在于,为治理术提出的一般定义与其内容丝毫无涉。首先,为什么要干预?即使自我限制是自由主义政府性的本质,福柯也坚持需要“有度治理”,但干预仍然是必要的。为什么干预是必要的?
第一个原因是人口中的个人利益相互矛盾,甚至彼此对立。因此,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art libéral de gouverner)不得不精确地确定这种分歧在多大程度上不会对总体利益构成威胁。自由和安全必须同时得到保障,这就不可避免地预示着在行使任何自由的过程中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危险和风险,同时也要保护集体利益免受个人利益的侵害,反之亦然。第二个原因是,安全机制既是自由的主要“消费者”,也必须是“生产者”。福柯强调的这一悖论实际上是所有自由主义所特有的,但在自我限制的自由主义(libéralisme autolimité)中却更加严重。举个简单的例子,市场自由要求没有垄断,但这要求立法,以对竞争和市场主体的自由行为加以限制,而没有垄断要求(ce qui suppose)立法限制竞争和行为主体的自由行动。
因此,自由与安全之间的权衡必须是永久性的。一个重要的后果是,以此种方式构想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会导致控制程序(procédures de contrôle)的极大扩展,而这是与自由相对应的必要条件。政府的首要职能是监督一般的行为机制,但当监督失灵时,政府又必须进行干预。在这个问题上,在《规训与惩罚》中形象如此突出的边沁再度出现,“全景式监狱”似乎成了自由主义治理的形式(formule)。
因此,自由主义治理术这门新的技艺意味着它与自由之间复杂的、甚至是模棱两可的关系,因为它必须创造自由,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也面临着破坏自由的风险。尽管福柯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本身并不能定义治理的实践,但他并没有为勾勒“良好的干预”( bonne intervention)的精确定义,提供任何线索。福柯多次强调了推理(raisonnement)所指向的唯一方向,即诉诸功利主义,在他看来,功利主义不再是组织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是(限制)治理的一项技术。有了功利主义,计算(calcul)就成了治理的唯一理由。“治理的理性必须尊重这些限制,只要它能自己估算出这些限制是其目标的函数,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手段”(NBP,13页)。治理理性(鉴于估算的重要性,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超理性(hyper rationalité))这一主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治理术几乎成为自然现象客观化(une objectivation de phénomènes naturels)的直接结果。福柯对此非常感兴趣,他在18世纪的海洋法(droit maritime)和《永久和平计划》中发现了这一现象,而最后一课,即1979年4月4日的课程,正是在“通过理性进行治理的技艺(art de gouverner à la rationalité)”这一理念的基础上结课的。然而,这些历史实例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实际上体现的是自然主义和自然秩序的思想。另一方面,提及功利主义和计算,却对自由与安全之间的权衡之难只字未提,而这正是自由主义治理的核心问题,它导致作者提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建议,如边沁的“全景式监狱”令人吃惊地被重新放回到安全配置的核心位置,而在书的前半部分,恰恰相反,确立安全机制意味着抛弃“全景式监狱”。这些难题的关键在于上文已经提到的问题:我们如何为政府干预设定限制,即一旦背靠权利进行抵抗不再被承认,我们如何保障人口的自主权?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从1979年1月31日的课程起,福柯绕了个弯,转而分析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的德国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éralisme)和战后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这两种政治经济学为干预问题提供了相当激进的解决方案,但它们修改了福柯最初的假设。尤其是它们假定了利益的自发趋同,而安全机制则捕捉到了利益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1948年,德国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重建,因此干预主义政策,尤其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占了上风。然而,1948 年4月,英美区德国管理部门的科学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相反的建议:“指导经济进程应尽最大可能得到价格机制的保障”,这一建议让人想起1774年9月杜尔阁关于谷物贸易自由的著名法令。自由主义的这一定义是由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顾问们起草的,艾哈德是本届政府的领导人,他将这份报告作为其工作的重点。这些经济学家组成了“秩序自由主义派”(ordo-liberals),其起源可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根据他们的说法,自19世纪末以来,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在某种程度上害怕自己会取得的成功,因此在经济现象的国家管理领域中创造了干预技术,以限制自由主义的影响(inventa une technique d'intervention dans la gestion étatique des phénomènes économiques pour limiter les effets mêmes du libéralisme)。哈耶克和罗普克(Röpke)等思想家明确解释了他们的主要理论所引起的一场“政变”,即认为纳粹制度不是极端危机状态的后果,而是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的逻辑延续和最终演变点。自由秩序派从纳粹经验中吸取的教训是,与其接受由国家监督和限制的自由市场,不如将市场的逻辑普遍化,使其成为国家的调节器。我们需要与18世纪和19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决裂,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让经济自由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扩展竞争和市场逻辑的问题。然而,如果认为建立自由市场就足以推广竞争机制,那就是“自然主义的天真”(naïveté naturaliste)。要使竞争在社会中发挥核心作用,自由主义政府必须积极干预。“因此,竞争是治理技艺的历史目标,而不是需要尊重的自然事实”(NBP,124页)。因此,公权力的干预必须完全致力于为市场的存在创造条件,使这一微妙而高效的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任何其他目标(充分就业、购买力、国际收支平衡等)都只能是次要的。同样,政府的职责也不是事后纠正市场对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政府必须对社会本身进行干预,以确保竞争机制发挥其调节作用。
福柯认为,这种创新思维催生一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即企业资本主义(capitalisme d'entreprise),在这种资本主义中,每个经济主体或家庭都被同化为一家既自主又负责的公司,这样个人就不再与他或她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相疏离。这种“企业”形式的普及使秩序自由主义有别于古典自由放任主义,后者的经济人本质上是交换的伙伴。它的目的当然是将经济调节作为社会关系的模式,但同时也是将一整套与企业相关的价值观(个人独立、道德责任等)置于社会生活的核心,与竞争机制的冷漠相对立,用罗普克的话说,“从道德上和社会学上来看,竞争与其说是一种统合的原则,不如说消解的原则”。因此,政府的干预应该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国家实施“社会政策”(Gesellschaftspolitik),让市场脆弱的竞争机制得以运行。这种“社会政策”(politique de la société)有助于市场的形成,例如促进财产所有权的获得,或帮助以个人保险取代集体社会保障。在这个自由社会中,竞争不再只是商人之间的竞争,而是公司之间的竞争。
因此,经济成为政治建设的参照——经济产生国家所需要的合法性,经济伙伴之间的自由产生政治共识——同时也是社会纽带,甚至是文化价值观的参照。从这个确切的角度出发,尽管论据不同,德国秩序自由主义逻辑性地发展下去,产生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尤其是芝加哥学派,它是对杜鲁门至约翰逊时期美国新政和社会计划的一种反动。尽管它与美国思潮的激进主义有很大不同,但与德国传统有许多共同点,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这两个学派都认为市场经济分析可以推广到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个人被视为自己的企业家。这些经济学家,如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以及备受福柯关注的支持人力资本理论的经济学家,将经济分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例如,每个人都会决定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以积累日后用于创收的人力资本,或者在犯罪行为的预期收益与刑事制裁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
这种普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框架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允许对政府行为进行检验,接受量化批评的考验。现在,人们可以根据政府行动在实施竞争和市场力量方面的有效性来对其进行评判。与18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相比,经济在分析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表现在,经济不再仅仅是更普遍形式的治理术的模型或例证,而是成为了卓越的治理术。因此,我们可以为政府干预下一个更精确的定义和内容:政府必须为市场经济和竞争的运行创造条件。政府干预的限度包含在定义本身中,因为将社会描述为一个自由竞争和利益趋同的领域意味着政府干预只关注市场存在的条件,关注其法律框架,而不关注其经济内容或社会后果。这无疑是福柯所推崇的“节度治理”的最佳定义,它既没有那么宽广的抱负,也与社会有更大的距离。秩序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采用了人口概念,但方式更为激进,赋予公权力调节社会的任务,保证社会的自主性,确保公权力(几乎)无需再进行干预。
实践与真言体系
福柯在撰写他的自由主义治理史时,一再表示他不想从政治哲学的普遍性(universaux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如主体、国家、公民社会等)入手,而是要从具体实践及其被反思和合理化的方式入手。这一计划在第一阶段,即研究18世纪时得以部分落实,因为正是借助分析这些具体实践,福柯证明了功利主义自由主义(libéralisme utilitariste)的存在。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严格来说,就福柯所依靠的政治经济学蓝图——即自我限制的自由主义,他未能成功阐明它在其中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部分。
因此,梳理从18世纪到20世纪自由主义的历史,有助于从理论上解决这两本书提出的核心问题,即治理的自我限制,但这一历时性的研究导致了一个新的问题:与现实的关系。第二阶段主要研究德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这一部分事实上没有了实践的身影,只剩理论——有限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 limitée)——的阐述,这是一种与“做事方式”(manières de faire)脱节的论述。
福柯的另一个尝试是将表象史(histoire des représentations)锚定在实在史(histoire des réalités)中,即运用“真言制度”(régime de véridiction)这一概念,我们知道这对于福柯更广泛的“思想体系史”(systèmes de pensée)计划至关重要,无论是关于监狱、精神病院还是性问题,都是如此。研究“真言机制”的历史,就是着眼于能向人们指明真理的思想体系,对这些思想体系的影响做出研究。福柯提醒我们“记住医生们在性或疯癫事情上说的所有谬误,这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唯一重要的是确定主导他们的真言体系……这一体系将我们现在知道也许并不那么真实的某些事情肯定为真实。”然而,福柯认为,从18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各种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为了治理粮食短缺,自由市场正在成为当代人“一个我称之为真言化的场所”(NBP,34页)。政治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所表达的真理正在取代重商主义所要求的一系列不确定的治安管理干预(interventions de la police)。福柯巧妙地利用了语义上的模糊性,因为当时的经济学家使用“真实价格”(prix vrais)这一表述,正是为了指代在自由市场上获得的商品价格,这些价格被认为是真实的,因为它们不仅使个人行为变得有效,也让政府的做法变得有效,因为它们都符合保护人民免受饥荒或生产更多财富的这一类共同目标。
福柯强调这些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方面,市场的真理性(vérité)是支持治理实践的自我限制的最有力的论据之一,另一方面,真言制度的原则赋予了政治经济学对事件进程le cours des choses的效力和作用。但是,这一原则是否如福柯所想的那样适用于政治经济学呢?这是值得怀疑的。虽然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接受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会影响经济政策和市场组织,但更难接受的是,这种政策的效果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观察到的结果来衡量。这与精神病学等学科存在本质区别。精神病学的论述是规范性的,它以真理的标准来界定疯狂与正常的区别,或正常性行为和与不正常性行为的区别,因此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大的直接影响。但是,政治经济学虽然可以规定自由政策,却无法控制其影响。如果说“真实价格”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只有在市场均衡的方法中才有意义,那么它又是什么呢?“真实价格”本身的抽象性使得它很难被赋予经验性内涵(contenu empirique)——即便某些经济学家尝试这么做——这就使人们对它是否可以将治理政治(politique gouvernementale)化为参照指数(indexter)并加以限制,都产生了疑问。抽象来看,市场是一个真言化原则(principe de véridiction),这与自由主义理论的雄心是一致的;但是,市场产生的数据所表达的真理,能够成其为真言化例证(instance de véridiction),进而限制政府,这种断言显然夸张了。我们无法断定福柯如何看待经济理论,也无法断定他对经济理论的评价是什么,但是,他很在意经济理论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误解了经济话语的特殊性,因为经济话语与现实保持着复杂的联系,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如此。
同样,他将自由主义对主权的批判纳入了自己的思考,但由于他早已有过思考,所以他对这一做法不会显得那么勉强。
统治权
对统治权的批判是福柯对权力问题长期思考的核心,目的在于构建一种从根本上摆脱统治权模式(modèle de la souveraineté)的统治思维方式。他曾多次解释过这一点,其中最著名的是《必须保卫社会》(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一书中1976年1月14日和21日的两堂课,这两堂课被明确表述为“对统治权理论的某种告别”(《必须保卫社会》,37页):
因此,对我来说,问题就是越过和避开统治权和个人对这种统治权的服从这个法律的中心问题,从而突显支配和奴役问题,而非统治权和服从问题。(《必须保卫社会》,24-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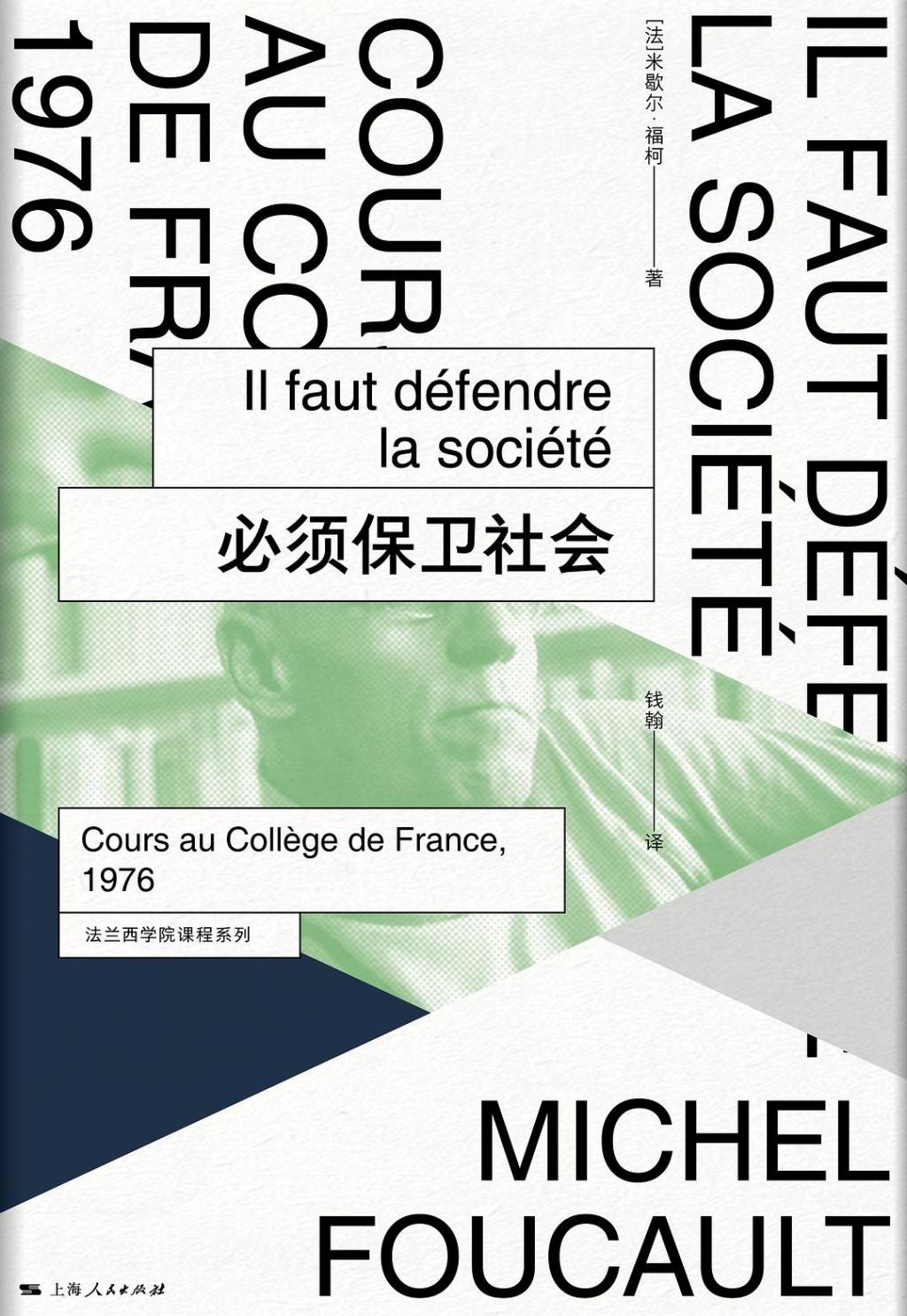
《必须保卫社会》中译本
但在福柯眼中,统治权是什么?这本质上是一个法学问题,即权利问题:一方面是臣民放弃他们让渡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统治者获得的权利,他以臣民的名义行使权威。福柯在许多场合都坚持这一法律维度,并将其视为统治权模式的构成要素:主权模式抓住了“法律形式的权力”(le pouvoir sous une forme juridique)。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把这种法律形式的从属关系,称之为服从(obéissance),而非奴役(assujettissement),其前提是臣民默认权威机构的合法性主张。其结果是,权力并不强加干涉,以臣民本来面目加以统治,并不试图窥探他们的良知或纠正他们的灵魂。这种权力主要通过不连续的征税制度(système de prélèvements discontinus),对财富和财产采取零敲碎打的行动——税收就是其中一项典范。但是,福柯所感兴趣的是其中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力,即规训权力(pouvoir disciplinaire),它不是通过偶然的截取(prise momentanée)而是通过严密而有持续性的分区控制(quadrillage ),通过纠正系统和监视系统(systèmes de correction et de surveillance),榨取劳动,制造永久的屈从(soumission perpétuelle)。这种权力的运作模式与统治权截然不同。统治权关心的是君主的荣耀,而惩戒权旨在制造臣民(fabrication des sujets)。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对法律的否定反映了福柯对理解权力现实的痴迷,不是从所谓权力行为的合法性角度,而是从权力与身体本身的接触中改变主体的有效性的角度来理解权力。“我们必须在利维坦的模式之外,在司法统治权/司法君权(souveraineté juridique)和国家体制(institution de l'État)划定的领域之外研究权力”(《必须保卫社会》,30页)。
正如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当福柯转向研究安全机制时,他对法律模式的批判变得更加强烈。我们看到,他强调了这些机制的逻辑与法律逻辑之间、市场与契约之间存在的距离。这导致他就契约和市场的异质性提出了一些会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迷失方向的建议(《必须保卫社会》,279页)。福柯告诉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因为在法律主体中,契约纽带预设了放弃某些权利以换取其他权利的保留,他称之为“转让原则”(principe du transfert,《生命政治的诞生》,278页)。然而,在经济领域,情况则完全不同:经济人从不放弃任何东西。他在任何时候都完全忠实于自己的利益,利益自始至终都在指引着他:“每个人不仅能够追随自己的利益,而且每个人必须追随自己的利益,一直追逐到底,寻求最大化利益”(《生命政治的诞生》,279页)。对司法的重新批判并没有导致统治权的完全消失。在分析中,统治权只扮演边缘性的角色,就像一个背景,不再引起福柯的关注。即便他写道:“统治权问题没有消除,相反,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STP,110页),但在他的思想现实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情况并非如此。现在看来,统治权只能作为治理的附属装置出现,完全是为了服务治理而设计的:“鉴于(存在)一种治理的技艺,鉴于它正在展开,[这是一个]看我们[将要]能够赋予主权以何种法律形式、何种制度形式、何种法律基础的问题"(《科学与技术》,110页)。关于统治权,福柯他就说了这么多。
不存在经济统治权
然而,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更进一步。在这本书中,他在否定统治权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最终的一步。他这样做,部分是基于一个受哈耶克启发得以形成的一个论点:“市场经济摆脱了所有总体化的知识(L'économie de marché échappe à toute connaissance totalisante)”。哈耶克认为,我们确实可以解释竞争运行的抽象原则,但是,却无法解释某一个特定经济局势(conjoncture économique)下的具体事实或实践环境(circonstances pratiques),因为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由无穷无尽的局部变数(adaptations locales)所组成,不可能对其进行思想上的概括,因为对最简单的经济状态的完整描述都会涉及数以百万计的相互作用,需要调动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人脑所能掌握的信息量。因此,经济世界是不透明的。“它本质上是不可总体化的”(《生命政治的诞生》NBP,285页)。因此,国家不具备有效干预的认知手段。国家的干预遭遇了市场经济的复杂性。结果,统治权/君权管理经济过程的能力被彻底剥夺,不是因为它没有这样做的权利,而是因为它没有这样做的能力:“你不能(这么做)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不可能知道”(《生命政治的诞生》NBP,286页)。
从根本上说,自发秩序或多变秩序(modèle de l'ordre spontané ou catalectique)的模式是这里的参照。福柯认为,竞争机制本质上排斥严格的私人利益之外的任何干预。市场世界过于复杂,不可能成为蓄意行动的目标。国家行动不仅不是竞争性监管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而且对竞争而言,这种行动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这部分分析的最后,福柯提出了一些关于经济统治权无用性的非常有力的主张:“经济学是一门没有整体性的学科;经济学一开始就证明,以统治权角度看待其所治理的国家之总体性,这不仅无用,也绝无可能。”(《生命政治的诞生》NBP,287页,与中译本的译文有所调整)。福柯得出结论,不存在“经济统治权”(souverain économique,《生命政治的诞生》NBP,286页)。这种对外部性(extériorité)和超越性(transcendance)的谴责不仅限于国家行为。它的矛头还指向任何为了给自己的行动赋予集体目标,而忽视个人利益的行为者。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坚守自己的角色,并严格遵守,即“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如果少数人放弃了这一行动路线,转而关心整体利益,这只会导致过激行为。所有这些分析得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即在经济学中,我们必须秉承曼德维尔的传统,始终赞成短视和“短期打算”(vues courtes ,《生命政治的诞生》NBP,284-285页)。“对所有经济行为人而言,模糊和盲目都是绝对必要的”(《生命政治的诞生》NBP,第283页)。而当国家自称具有长远眼光时,它看到的却是“幻想”(chimères)。
这种对视野(regard)和能见度(visibilité)的分析极不寻常。我们不能不将其与福柯对“全景式监狱”的反思联系起来,将其视为“全景式监狱”的对立面。新自由主义经济描述了一个个人的世界,他们不仅目光短浅,只能从他人那里感知到愿意向他们传达的价格,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受任何中央监控的约束。一方面,我们有一种控制一切的力量,因为它能看到一切,知道一切;另一方面,我们又有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力量,因为它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知道。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鲜明的对比了。
货币
然而,有一个基本的市场现实是这种自由主义的非整体经济概念所无法整合的,这就是货币关系。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考虑一下围绕货币的立法机构。它对竞争秩序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货币的发行权是一种只有中央银行这一特定机构才享有的垄断特权,另一方面,法定货币又迫使市场参与者在交易中接受货币。垄断和强制——与竞争和自愿交换的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相去甚远!再加上货币与权力之间数百年的联系,这幅图景必然会让任何自发秩序的拥护者望而却步。有了货币,“看不见的手”的理念就会受到质疑:市场秩序的总体化以一种明显可见的形式出现,即货币政治(politique de la monnaie)。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自由主义思想都将(neutraliser)货币中立化作为自己的目标。我们所说的“中立”,指的是一种概念框架,它接受这种与竞争规则背道而驰的制度性存在,但又能在这一存在丧失对现实的影响后顷刻建立起经济关系:它不会改变经济关系的竞争性质。为什么不会呢?因为货币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就像语言一样,它使我们能够在不干扰信息内容的情况下进行交流。如果货币发行量增加一倍,所有的价格都会增加一倍,因此不会影响任何基本因素,不会影响商品之间的汇率,也不会影响生产或就业水平。说货币是中性的,正是这个意思。或者再换一种说法:货币是一种纯粹的工具,其目的是使交易更容易,而不改变参与者的实际情况。还应该记住的是,市场经济最先进的形式化,也是当代经济思想的深层结构,即瓦尔拉斯概念(conception walrassienne),提出了一种没有货币的市场分析。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货币相对于自由主义的竞争秩序概念来说是多么陌生了。
福柯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与这一分析不谋而合。货币(monnaie)和铸币(argent)都没有出现在索引(index)中。甚至货币与统治权之间已被证实的密切联系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当他想象经济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时,他考虑的是一个完全由市场构成的世界。但是,货币既不是次要因素,也不是中性工具。它是统治权在经济学中的具体形式(forme spécifique)。正因如此,自由主义者对货币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本文的论述中,重要的不是对这些理论进行深入探讨。相反,我们想要解释的是,福柯对哈耶克议题的特定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他对统治权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错误认识。在1979年1月31日的法兰西学院课程中,他关于联邦德国成立的分析,就是这一错误认识的表现。
如果说联邦德国的诞生深深吸引了福柯,使其几乎用了整整一堂课进行讲授,原因在于这个例子为思考一个有关限度的经验提供了契机,这不亚于在统治权行动之外形成一个共同体。这一事件的理论意义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从经验上验证了统治权无用论(inutilité du souverain)这一判断。联邦德国为福柯提供了一个社会的范例,其基础不是行使基于历史的统治权(droits historiques souverains)——在纳粹德国之后,德国人不再拥有这种权利,而是经济自由的制度化(institutionnalisation de la liberté économique)。福柯用一个强有力的表述,概括了这一点:“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确保经济的自由运转”(《生命政治的诞生》 NBP,85页)在缺乏历史权利和政治合法性的情况下,新的德国国家的基础在于价格自由和艾哈德于1948年6月对社会市场经济的认可。对统治权权力局限性(limites du pouvoir souverain)的理论分析在这里得到了非常典型的体现。福柯从中推导出了对一个社会的描述,这个社会可以说是“整体上是经济的”(intégralement économique),因为它是在统治权约束之外,它产生于统治权约束之外的自由交换这个游戏:
但是,只需假设——这也是艾哈德的文章所暗含之意——一个制度框架X,其性质和根源不重要。假设此制度框架X,其功能当然不是行使统治权,因为在当前情况下,没有任何东西能为法律的强制权提供基础,而仅仅确保自由。因此,该制度框架的功能不是去约束,而是去创造一个自由的空间,确保一种自由,即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现在,我们假设,制度框架X,其功能不是依据统治权实施强制约束,而只是建立一个自由空间,再假设任一数量的个体们自由地接受并玩起了这个由制度框架X确保的经济自由游戏,那将会发生什么呢?个体们践行着这种自由,不是约束个体的自由践行,而是给予其践行自由提供可能性。那么,这种对自由的自由践行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赞同此框架,意味着一致认同所作出的整个决议。这个决议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正是为了确保这个经济自由或确保经济自由成为可能的一切。换言之,经济自由制度不管怎么样理应、也能够具有虹吸管(siphon)的功能,起到像是催生政治统治权那样的作用。(《生命政治的诞生》NBP,84页)。
应仔细阅读这段重要的引文。福柯描述的共同生活的基础不是通过强制力(pouvoir de la contrainte)将领土内的个人联合起来的统治行为,而是经济自由制度。福柯告诉我们,自愿行使这种制度化的自由才能成为共同体的成员。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竞争实践理应带来经济福祉(bien-être économique)方面的益处。诚然,这种集体认可将采取一种政治形式,但就其动机而言,它并不具有政治性质。它是另一种东西,是对自由游戏的自愿遵守。正如下一节所要说明的,这涉及到对如下问题的思考,即公民社会是否有可能以完全自主的方式存在,而不需要依赖于专门的政治机构。福柯坚持认为,经济所扮演的这种特殊的、本质上政治性的角色自其起源以来就一直是当代德国的基本特征之一。
事实上,在当代德国,经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统治权,也通过它们明确依赖的制度和制度运转来产生政治统治权,而制度运转恰恰又使此种经济得以运转。经济为国家提供了合法性,而国家为经济提供保障。换言之。经济是公法(droit public)的创造者……(《生命政治的诞生》NBP,85-86页)
“经济是公法的创造者”( 《生命政治的诞生》NBP,886页)这难道不是自由主义的终极公式(formule ultime du libéralisme)吗?或者说,如果你愿意,这是对经济凌驾于法律之上、治理高于统治的肯定。经济产生政治符号(signes politiques)。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合理性证明(justification)。换言之,旨在借由垄断合法暴力,界定领土,并确保公民的集体支持(adhésion collective)的特定政治机构,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也可能不存在强制权(pouvoir de contraindre)。经济自由本身就能产生足够强大的效果,确保社会凝聚力和参与者的集体支持。经济自由所产生的一致性远胜于政治,因为政治总是倾向于分裂公民。经济自由通过创造比法律合法性(légitimité juridique)更具体、更强大的东西来实现社会凝聚力、信任、共识:“永久不变的共识,那些活跃在经济活动及其内部的代理人所产生的共识。投资人、工人、工厂主、工会,都是这类代理人。所有这些经济合作伙伴,就他们接受了这个自由经济的游戏而言,也就达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共识”(《生命政治的诞生》,NBP,第85-86页)。这就是西德国家的新的单一模式。它提出了一个没有统治权的国家,一个“彻底的经济国家”(《生命政治的诞生》,NBP,87页),将投资人、工人、工厂主、工会聚集在一起。最后,福柯曾预言会消亡的“统治权理论的法律大厦”(《必须保卫社会》IFDLS,33页)将消失殆尽,而纯粹的经济国家的概念应运而生。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一发展过程的极点(On est ici à la pointe extrême de ce cheminement au cours),而在这一过程中,福柯逐渐不再考虑统治权,而开始只谈论讨论治理:
我越是谈论人口,有一个词就越是出现:“治理”。我对人口谈得越多,就越不再说“主权”......事实上,治理远重于主权,重于统治,重于统领权(Imperium)(SPT,78页)。
然而,如果对1948年和1949年德国的经济形势进行更详细的研究,就需要进行截然不同的分析。
福柯认为,1948年6月24日的价格自由化是德国重新建国的高潮。正是从这一刻起,经济游戏开始启动,并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这一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历史问题,但更多的是理论问题。奇怪的是,福柯在分析德国复兴时,并没有提到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具典范意义的行动,即1948年6月20日货币改革。1948年6月20日星期日,新货币德国马克诞生,旧货币帝国马克(Reichsmark)被废除,并首次组织了每人40马克的分配。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疏忽,因为评论家们一致强调这一改革极为重要。因此,对于当代德国历史而言,1948年6月20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也是德国的诞生日。事实上,德国马克的引入标志着未来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其意义远大于德国马克在1949年正式生效。还应指出的是,第一个在所有三个西部占领区开展业务的机构是德意志银行(Bank Deutscher Länder),即以后的中央银行。换句话说,德意志银行是联邦德国机构存在的第一种形式。它的成立比第一届联邦政府的成立早了18个月。尽管福柯的分析侧重于 1948年6月24日的法律,但其标题“货币改革后的管理原则和价格政策法”(Gesetz über Leitsätze und Preispolitik nach der Geldreform)——就清楚地表明它是货币改革的结果。只有进行了货币改革,这种自由化才有意义,才能有效。正是由于消除了过多的货币,价格政策才得以有效。货币改革确保了价格的合理性。然而福柯对此却只字未提。
那么,在1948年的货币改革中,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其中重要性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来获得一个初步认识,即这不是德国倡议的结果,因为正如福柯正确指出的那样,从1945年5月起就不再有任何德国行政机构,更不用说政府了。它是由西方阵营的主导力量——美利坚合众国——构想并实施的一项行动,美国将其强加给了英国和法国的合作伙伴。换言之,货币改革是由占领国军事强权推动的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西方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对抗共产主义政权。这是最纯粹的统治权形式。对此,所有参与方都非常清楚,而苏联是最主要的反对者。他们的抗议基于1945年8月签订的《波茨坦条约》中的一项规定,即德国应“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经济体(une seule unité économique)”。针对这一货币政策,苏联要求宣布封锁柏林,直接目的是禁止德国马克的流通。这证明了货币问题的重要性,及其与统治权和领土问题所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随着德国的货币改革,德国的分裂以及冷战注定将成为现实。
没有什么比柏林问题更能说明货币改革的性质及其重要性了。盟国完全清楚苏联会反对这一改革,因为改革将通过使西区自治,分裂德国,因此盟国最初将柏林排除在改革之外。他们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四方协议,根据柏林的特殊地位和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统一柏林的货币。因此,在1948年6月20日的纸币兑换中,每个德国人都获得了40马克的初始配额,但其中并不包括柏林。亲西方的西柏林人对这一限制不无忧虑,他们在恩斯特·路透(Ernst Reuter)的率领下,要求将西柏林完全纳入西方经济体系,这意味着共享同一种货币:“拥有货币就是拥有权力”。苏联对货币改革做出了回应,禁止在包括大柏林地区在内的整个地区使用西德马克,并创造一种与之竞争的新货币。苏联军事官员宣布,在西区发行的纸币不得在苏联占领区流通。因此,他们开始封锁柏林。苏联军事官员还宣布在苏区发行新货币。西方人立即拒绝让这些决定在他们的地区实施,最终决定采用新货币,并在其上盖上B,以与德国马克作区分。但他们也允许苏联货币在其占领区内流通。没有比这更能表达货币与统治权之间的内在联系了:冷战的第一个战场就是货币问题,这关系到亲西方德国的存亡。确定由谁发行纸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明确谁是统治者/主权者的问题。
上述简要分析清楚地表明,西德不能被视为一个彻底的经济国家。其根源在于美国的介入及其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考虑到这些,那么,有度治理的问题也完全是一个次要问题,甚至根本不重要。在该问题上,福柯似乎严重低估了最经典的统治权政治秩序(ordre de la politique de souveraineté),即权力斗争的秩序。德国人在其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这也可以说明德国马克是纯粹统治权行为的产物。德国专家只是在“罗斯威森会议”(conclave de Rothwesen)上被召来,起草具体规定改革技术条款的文本。因此,与福柯的看法相反,我们必须认为1948年的改革具有政治目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这项改革所产生的再分配效应(effets redistributifs)的重要性,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而这与货币中立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简单地说,所有货币储蓄都大幅贬值,而实物资产(资本、不动产、生产工具)却普遍幸免于难。迈克尔·休斯(Michael L. Hughes)将其描述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没收之一,其规模堪比苏联的农业强制集体化。
由于福柯坚持的概念框架将货币视为中性的交换工具,因此他将货币改革通过再分配效应而产生的重大政治分歧完全抛在了脑后。货币改革引发了广泛的辩论和争论,造成西德政治体制的严重分裂,这与以下经济博弈形象相反:在福柯的分析中,经济博弈中参与者(投资人、工人、工厂主、工会)因其利益得到满足,故此表达了一种集体同意,并围绕竞争力,实现了和谐。改革被认为是特别不公平的,因为它没有影响到不动产,而只是使得那些借由货币表达的权利(droits exprimés en monnaie)贬值。这与福柯所谓的自发同意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当他审视竞争游戏时,却从未提及这种游戏可能会产生分歧,例如在工资方面就会出现分歧。就经济形势而言,价格自由化后出现了一些重大问题。1948年11月12日,900多万德国人在德国工人联合会(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的号召下,罢工24小时,抗议高昂的生活费用。因此,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初,就认为达成永久共识,这种看法并无根据。随后,良好的经济成果无疑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它们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集体支持。
巴登哥德斯堡会议和自由主义政府
米歇尔·福柯研究了1959年,在著名的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上,德国社会民主党认可社会市场经济的做法,借此有力地证明了秩序自由主义的分析在西德政治合法性概念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首先与从背叛的角度论述这些事件的经典分析保持距离,这种分析在他撰文时在左派和极左派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谴责将社民党提出的在社会市场经济框架内建立“公平社会秩序”的可能性视为掩盖其倒退的虚伪。福柯的看法并非如此,他写道:
但是,对于用另一只耳朵来听同样这些句子或者从另一种理论“背景”出发的人而言,这些词——“公平的社会秩序”、“一种真正的经济竞争的条件”——意思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们表明了对于一整套理论与纲领的拥护,而这一整套理论与纲领不仅仅是关于市场自由的效率和效用的经济理论。它还表明了某种类型的治理,也正是通过这种治理,德国经济才充当了具有合法性的国家的基础。(《生命政治的诞生》NBP,第90-91页)
福柯根据他刚才对联邦德国的考察,分析了社会民主党对新自由主义的拥护。他的论点如下:德国的状况使我们面临着一种倒置的情况,因为“相比于国家而言,经济是根本性的,而非国家作为这种或那种经济选择的历史—法律框架而位于第一位”(《生命政治的诞生》NBP,91页)。但是,由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经济规则本身,即自由主义治理,因此接受这一逻辑是参与政治游戏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巴特戈德斯贝格会议上,社会民主党必须坚持德国政治和经济的基本共识,即经济增长,才能参与德国自1948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治理游戏。1979年,当法国左翼站在政治权力的大门口时,福柯走了很长的路,他坚持认为不存在社会主义政治理术(《生命政治的诞生》NBP,93-95页)。他承认社会主义有“历史合理性、经济合理性和行政合理性”,但没有自发的治理(gouvernementalité autonome)。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要想存在,就不得不利用各种治理类型。
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分析欧盟是很有诱惑力的。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经济与政治的倒置,以及同样的货币统治的基础作用。此外,正如《宪法条约》草案再次表明的那样,竞争准则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更广泛的政治体制概念中,也发挥着结构性作用。正如福柯在谈到联邦德国时所写的那样,问题不再是国家将允许经济享有何种自由?相反,从为国家合法性提供有效基础的意义上看,经济自由如何才能具有国家的功能和作用(《生命政治的诞生》NBP,95-96页)?总之,自由主义治理无疑是研究欧洲局势的一个关键概念。
自由主义的政治目标
这种批判性的解读在很多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让我们感到,可能我们忽略了福柯思想的基本要点。真正的问题无疑在别处。为什么这位哲学家对自由主义的这种特殊形式如此感兴趣?为什么对德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不加批判地进行利用?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这出自福柯这样的思想家。为什么要对没有主权的经济和政治进行危险的探索?
主人与权力
从第三课开始,福柯就向听众解释说,他在以前的著作中研究过与法律制度相关的规训机制的特殊性,他打算在这门课中反思规训与安全机制之间的区别。他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打断不断提到主人、单调地论证权力的窠臼”couper court à l'invocation répétée du maître et aussi bien à l'affirmation monotone du pouvoir(《安全》STP,57页)。这一论断首先反映了他意识到从纪律和强制的角度来思考社会秩序的局限性和不足,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最近才出现的治理形式。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将18世纪以来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普遍概念,一种在与社会规训化(disciplinarisation de la société)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人权。福柯认为,自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是一种权力技术(technique de pouvoir),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对此,可以有两种政治解读。第一种是狭义上的“福柯式”解读,即将这句话视为一种警告。毫无疑问,权力把自由留给人民(population),目的是为了控制,现代治理术赋予我们自由,目的是为了规训。安全机制既制造了自由,也消耗了自由,这一事实也说明了这一基本观点:自由取决于权力。而第二种解读则坚持认为,既然治理必然是对自由的保护,那么它就构成了一种值得反思,并能引起某种关注的权力形式。这两种解读都是可能的,我们可以认为福柯可能同时考虑了这两种解读。然而,贯穿这两篇演讲的反思性张力倾向于表明,福柯倾向于第二种解读,即使从未明确表示过。
他对国家的思考提供了一条线索。忠实于之前的研究方法,福柯拒绝诉诸于政治哲学这样一个一般性的范畴。国家不是一个普遍的概念(universel),它没有本质:要理解它,我们必须“走出去”(passer à l'extérieur),通过实践(即权力的一般技术)来理解它。正是为了避免“循环本体论”(ontologie circulaire)的风险,国家的谱系必须建立在治理理性的历史(une histoire de la raison gouvernementale)之上。表面来看,这一论点只是一种方法,但也让福柯对那些以国家倾向于获得无限权力或其扩张在历史上不可逆转为借口而谴责国家的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种概念过于简单化,因为它实际上等同于将国家虚构化,赋予其本质。福柯将这种方法的源头定位于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论述后来在不知不觉中被20世纪70年代批判左翼、极左派的人采纳,他们将任何对国家作用的肯定,都视为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autoritarisme),甚至法西斯主义。福柯认为,这种立场是不可接受的,原因有二点。首先,国家对社会事务的干预从一开始就被限制在自由主义治理所提出的构架中。第二,国家的干预是建立自由所必需的。
主体自治(Autonomie du sujet)与自由主义
福柯对治理术的这一谱系反思的真正目的无疑不是治理术本身,而是为主体自治提供一种可能的阐释。他选择的路径是通过自由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这种着眼于特殊形式的自我限制的自由主义治理术。正如我们所说,这两门课程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奠基性的尝试。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特殊的道路呢?因为福柯认为,这种形式的权力为维护主体自治提供了最好的保障。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它们贯穿了整本书,却从未被系统地介绍过。这种论证的实验性和临时性特质只能促使福柯保持谨慎。
原因之一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诉求(revendication de scientificité)改变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重商主义绝不声称自己是一门科学,它与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与普通人无法了解的统治的秘密(mystères du gouvernement)联系在一起,而经济科学则可以由任何人建立或验证,即使他们不是统治者,因为科学的目的是成为常识(connaissance commune)。因此,权力不再垄断知识和真理,相反,正是知识的需求从内部(de l'intérieur)划定了权力的界限。
然而,主要原因在于自我限制的自由主义所确立的政治对经济的依赖性。然而,经济凌驾于政治之上非但不会构成毁灭性的压迫,反而是维护主体独立性的最佳保障。在福柯的思想中,这一主题只是渐次出现,但是一旦得到强调,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我们所说,经济学是一门没有整体性的学科,这一论点的本质即在于此。福柯在分析哈耶克和18世纪的思想中,找到了构成其推理的主要元素,他认为,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谴责……主张经济过程存在政治整体化的谬论(le paralogisme de la totalisation politique du processus économique)。”因此,国家的盲目性十分明显,这并不是因为它为了政治目的而选择盲目,因为政治目的总是可以修正的,国家盲目的原因在于它对于经济现象的认识总是有限的。国家不能直接地和普遍地进行干预,不是因为它没有权利这样做,也不是因为它做出了不能这样做的契约性承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不知道如何做。在最后第二节课,福柯讲述了一个重要结论,即包括国家在内的任何代理人(agent)都无法以集体利益为目标,更不用说实现集体利益了。这意味着存在一个任何统治者、任何机构都无法到达的孤悬之位;没有人比个人自己更清楚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以及自己应该怎么做。福柯坚持认为,这一孤悬的位置具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根本性,其重要性当然在于,在福柯看来,每个人必须能够表达和保护的利益和独特性(singularité)可以从经济领域拓展到一般的行为领域。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特别感兴趣。首先,虽然这些作者追随哈耶克,认为任何经济整体化都是不可能的,但他们也坚持认为,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可理解性框架(grille d'intelligibilité)完全是通过成本—收益的反思形式进行思考的,因而这是一种经济学形式。因此,“经济人”是权力与个人之间的唯一界面(unique interface)。福柯在课程的最后部分才使用“经济人”这个概念,但与他关于自我限制的治理的探究,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仅局限于其经济维度,而是意味着经济维度,也只有这一维度,可以用于分析各种类型的行为。对罪犯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新自由主义者研究罪犯时使用的工具与他们理解其他任何个人行为时使用的工具相同(“罪犯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什么不同Le criminel n'est rien d'autre qu'absolument n'importe qui”,《生命政治的诞生》,NBP,258页),因为他们使用的分析框架(grille)完全是经济的,从效用计算的角度分析罪犯的行为,换言之,与用来衡量普通人的理性框架相同。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政治受到经济偏见的制约,而政治正是通过经济偏见来认识社会的,我们怎么能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保护每个人的身份、更尊重各种差异或偏好的体系呢?
在反思的最后,福柯从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在《公民社会史论》(1767年)中提出的公民社会概念中找到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缺失的联系。由此,他便能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如何治理一个由经济主体组成的社会?在弗格森的著作中,福柯看到与几年后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问题类似的政治问题。在这位苏格兰哲学家看来,公民社会基于两个要素。首先,它是个人自发合成的产物,不需要任何明确的契约,也不需要通过臣服契约构成主权。对他人的一系列无私情感,如同情、仁慈、怜悯(但也有对他人不幸的吸引)或对同一共同体的归属感,确保了这种聚合(synthèse)。其次,与自然法一样,在任何政治体制之前,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拥有权力和指挥权的事实就存在于自然状态中。弗格森说:“对人来说,从属制度(système de subordination)与社会本身一样重要。”这是一个基本论断,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绕过契约理论固有的难题。正是在这样构成的公民社会中,经济纽带被铭刻了下来。这既解决了权力问题,也解决了社会的凝聚力问题,这要归功于利益自发趋同的一致性原则。
国家或政府如何融入这一格局?面对一个已经构成的、“一切既定”的社会,国家或政府的地位如何?福柯颇为谨慎,没有给出答案,或者说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给出了答案,他引用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对美国人民说过的一句话:“不应该混淆社会与政府。社会是由我们的需求而产生的,而政府是由于我们弱小而产生的……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必要之恶,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是不可容忍的”(《生命政治的诞生》,第313-314页)。
福柯的论述到此为止。权力和政府实际上被排除在外,这便是实验的终点。但是,这场实验发生的条件却极不可能:福柯并没有认真对待罗普克、哈耶克和贝克尔的经济学论述,尽管他们的论述仍有许多欠妥之处。但是,福柯的确探索了这样一项自由主义议程可能成形的抽象条件。毫无疑问,福柯也意识到他自己也经常无路可走。
这场经历收效甚微,但也留下了一些痕迹。“强硬的”(dure)自由主义之路,即那些不妥协的经济学家所选择的道路,这为某些问题的推进,提供了相当具有吸引力的思路,因为它以一种尊重差异性(différences)的政治,取代了惩戒性社会(société disciplinaire),这是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即使从简单的理论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在福柯的政治思想中,这种对异端(hétérodoxies)的尊重无疑比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他在1979年3月21日演讲的最后,在概述他所勾勒出的分析的前景时,强烈地提到了这一点:
在上述那种分析视野中所出现的,完全不是构想或规划一个惩戒性社会——在该社会内部,各种规范机制从内部接续或延伸了束缚个人的法律网络。也不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一般规范化机制以及驱逐不可被规范者之机制都是必要的。与此相反,在那种视野下,我们怀有一个社会图景、观念或主题—规划:在该社会中,各种差异体系(systèmes de différence)得到最优化;在该社会中,摇摆不定的进程(processus oscillatoires)获得了自由空间;在该社会中,要容忍那些少数个体和少数实践活动;在该社会中,作用的对象不是游戏的参与者,而是游戏的规则;最后,在该社会中,干预的类型不是对个人进行内部约束,而是一种环境类型的干预(intervention de type environnementale)。(《生命政治的诞生》NBP,265页)
这一丰富的分析突然将焦点从经济领域转移到一般行为领域,浓缩了这两门课程的政治哲学精髓。因此,反思是开放的,其中不乏激昂的色彩:
自由主义将制造乌托邦的关切拱手让于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的活力以及历史生机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种创造乌托邦或者乌托邦式的活动。当然了,自由主义同样也需要乌托邦。我们要建造自由的乌托邦,我们要思考自由主义的模式,而不只是把自由主义看作治理技术的另一种选择。(《生命政治的诞生》NBP,225页)
最后这段引文被奇怪地以纲领的形式塞进了一堂课的中间,似乎是为了让它不那么显眼。为什么要如此谨慎呢?这可以归因于福柯思考中不可否认的实验维度,以及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他的作品极具挑衅性和偶像破坏的涵义。福柯的自由主义诱惑力,如果说展现了他令人惊异的自由精神——这一自由精神能够助其从他自己建立的思想形式中解脱出来,最终呈现出来的,不过是隔靴搔痒。
原文刊于《年鉴:历史与社会科学》(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2007年第5期,第1155-1182页。让-伊夫·格勒尼耶(Jean-Yves Grenier),法国社会高等研究院弗朗索瓦·西米昂社会和经济史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17-19世纪的经济思想史,著有《旧制度的经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交换世界》(L'Économie d'Ancien Régime : Un monde de l'échange et de l'incertitude, 1996)。安德烈·奥尔良(André Orléan),法国经济学家、法国社会高等研究院荣休教授,主张经济调控,研究领域为货币、财产、协约经济(Économie des conventions)和认知经济(Économie cognitive),著有《金融权力》(1999)、《暴力与信任之间的货币》(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