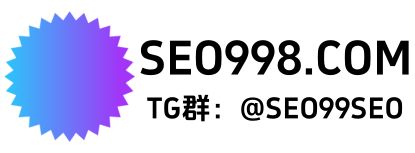中国财经时报网:扒开美女嫩嫩的尿口-记住那些阔大的女性力量
编者按:“每一个向上的台阶,负载的重量都是超预期的,每一粒收获中所浸润的汗水皆是饱和的。”即将过去的一年,大家都付出了超常的努力。澎湃评论部推出2024年度特别策划《让一束光点亮另一束光》,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都能向光而行,传递温暖、照亮彼此。
去年最后一日送走了母亲,我不再是谁的女儿,因此也就不再是孩子,心境陡然一转,衰老的感受如洪水袭来。一整年的意兴阑珊,成了一场“漫长的哀悼”。
2024年,我们还作别了这么多优秀而著名的女性学者:乐黛云先生93岁,叶嘉莹先生100岁,饶芃子先生89岁。乐先生和饶先生,曾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南饶北乐”,叶先生则是本时代“穿裙子的士”。这三个人对我别具意义,也许因为学科相近、或者是由地域之便,我都曾有幸与她们小有交集,亲炙芳泽、坐沐春风。我母亲虽不是学者,只是普通的教师,但也得享高寿89岁。这些年长的女性突然对我具有精神支撑的意义,我也有意无意总是在计算自己的年龄和她们各个人生阶段的距离,想来是因为我个人的时空焦虑吧?
眼睛突然就花了。
先是想算算韩愈说自己“而视茫茫,而发苍苍”时是几岁?钱锺书“病眼难禁书诱引,衰躯端赖药维持”呢?心里沮丧的时候想起苏东坡,他会安慰自己:“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我估计是老花眼或者飞蚊症,外部世界是看不清了,但他非要说内心的春花正灿烂。毕竟是苏子,我学不来。而且他们都是男性,还尚且如此,那女性不是更容易老吗?
有一长串光鲜又世界闻名的女作家、女学者的名字,但可恶的理性让我对她们都免疫!她们要么只是个教学内容、要么是阅读的对象、要么不过是个硬邦邦的理论符号而已,但作为一名身在高校的“女性学术人口”,我的处境是具体的。你说奥斯丁?狄金森?波伏娃?上野千鹤子?她们都没结婚好吗!夏洛特·勃朗特?抱歉,她不用接孩子。伍尔夫?拜托,她不仅不用接孩子,还不用上课、不用指导论文。
突然非常需要女性的榜样。那种扎扎实实、普普通通,和我一样困于各种社会角色中,还在专业领域绽放光芒的女性。因为乐先生、叶先生和饶先生的离开,我又看了很多她们的旧作、或者与她们相关的文章,重新确证了一遍她们对我的意义。慢慢我才想明白,她们的榜样力量不单纯只是专业能力的突出,更因为她们的力量是从普通、日常和充满缺憾的人生里超拔出来的,不是天生获得的。
叶先生曾带着八个月大的女儿寄人篱下,“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饶芃子先生一边教学一边写书,一边也要肩负教育孩子的责任,她的女儿在不久前的告别辞里,回忆母亲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温婉厚道”的“潮州姿娘”,让两个女儿都学会做饶氏萝卜糕……
她们是智识的,又是柔软温暖的,特别是都独有着女性的包容,在自己的职业场所,因为专业精神和无私的立场,发挥了重要的弥合分裂的作用。我愿意把这些,视作女性的特质与魅力。诗人痖弦曾回忆说,当年在台湾诗坛新旧派诗人是不往来,不一起吃饭的,但是因为叶嘉莹先生在,大家可以坐在一个桌子上吃粽子。乐黛云先生亦然。她一直主张“五湖四海”,对“门户之见”和“文人相轻”从来嗤之以鼻。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的饶芃子先生,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不如此,一位热爱文学的女教授就绝不会做好学校管理的工作。
如果止步于认识到她们和我们一样,在世上踩泥、吃苦、流汗(顾随先生语),只能觉得她们和我们亲近,但这还不够,因为她们还给我们力量。
首先是精神生活的优先性。她们和你我一样,要照顾家、培养孩子、侍奉自己中年以后总会各种病痛的身体,处理那些必须要面对的繁杂事务,但是在这些之中,她们永远将精神生活,放在了首要位置。叶嘉莹先生说不要假借隐逸去逃避世界,要心理上带有出世的平静,去积极做一番入世的事情,所谓:“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
请注意,她们不仅会做饭、会带孩子、会做家务、还会养猪、种菜,但是她们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没有用“密集母职”逼迫自己、没有用“贤妻良母”限制自己。叶先生在加拿大的图书馆小工作室里,为了节约时间读书做研究,甚至一上午都不去打水喝茶;她的冰箱里都是非常简单的速食或剩饭。乐黛云先生的书房堆满了书,凌乱中充满了书香气,因为书对她,不是装点,是工作的必备之物。饶芃子先生也一样。她们“选择”学者的逻辑,而不是家庭主妇的逻辑:她们不是先让房间窗明几净、再让书桌井井有条,然后做个烘焙给孩子,最后焚香净手、打开电脑。她们会简化日常,尽快投入工作和教学,她们选择对职业提出最高规格的要求,而不是个人生活质量。
其次,我发觉她们都有一种“神圣的单纯”(“sancta simplicitas”)。乐先生笑着回忆困难时期为了按领导要求,在不喂粮食的条件下养肥小猪,自己也干得非常起劲,每天漫山遍野地让猪拱食;此外,乐老师因为喜欢帮助贫困学生经常受骗,汤一介先生和学生们说起时,乐老师也一样笑笑,后来继续“屡教不改”。叶嘉莹先生晚年在接受一个著名的电视主持人采访时,被反复问到她的巨额捐款,她等不及去谈她的诗教多次被打断,竟直言不讳地说:“我本想和你谈学问,但看来你只关心钱!”正是她们这样的真纯、执着和简单,才能让这些女性学者心无旁骛,勇往直前。
最后让我感佩的是她们都以一种浓烈的生命情感,全情投入到一种超越自我的工作、特别是那些薪火相传的教育工作中。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是她们没有选择枯守书斋,理性经济地只为个人的学术精进。或许会有人批评她们的“学问”不够精深,但在人文学科上,到哪一个公认的程度算的“好”或者“优秀”呢?有人觉得乐先生掌握外语不够多,有人说叶先生诗论不够深,也有人觉得饶先生没有持续耕耘一个领域有些遗憾……抱有这些观点的人,或许都是带着高高在上的心态,用某种单一维度的标准,去评价一个丰足的、立体的、历史的人和她的事业。
可是文学、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以及教育事业,如何丈量长短、比拼高下呢?何况,她们将有限的时间,慷慨地交给了那么多学生,叶老师、乐老师不用说了,饶老师女儿回忆说,母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总是打扮停当,拿上包要去上课,对看护的阿姨说学生们等着呢!我想起我母亲的最后一段时间已不省人事,在床上的呓语中都是不断和学生说话,却不认识我。对她们来说,当生命的潮水渐渐褪去,她们抖落了所有的俗物,在记忆的沙滩上留下的,不是自己、不是钱财、甚至不是自己的儿女,而是她们总在耳提面命的学生、热爱诗文的听众。这难道不让她们超越了个人生命的有限吗?
因为人是必死的,所以时间对每一个人都如同一个线段,不是一条射线。在起点的年轻时代,觉得日子还长着,有无限的可能,但岁月流转,让你和时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线段的终点在变短,过去的一切变得沉重。但正因为这些尊者和长辈离去的背影,提示了你终点的临近,反倒确证和规定了你过去存在的价值。而此时此刻,你所面对的具体的繁杂、混乱和艰难,都不过是人生的必修课。唯有熬过去,才能挺过来。
这些阔大的女性力量,给了我们滋养和示范:让我们明白学者的身份,并不能成为女性免除家事、杂务、离乱的豁免牌,智识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逻辑、生命的有限、衰病的必然,但你仍然可以选择用精神生活去超越这些有限,将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一种前行的力量,去处理更宽广的社会问题和思考人类的处境,继而借此超越肉身的速朽。
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用诗意的方式展现了叶嘉莹先生的一生。她人生的蹇涩,用的是她的诗句和诗意来体现,而悲苦的细节,多是化作了几个空镜。我想,拉开历史的长镜头去看,你我此时具体的艰难,只会成为人生文本上被删除的字句,唯有盼望我们有幸能如这些逝者一样,留下一些生命的诗行……

海报设计:赵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