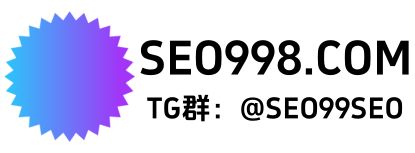苏珊·桑塔格逝世20周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在她之后,苏珊·桑塔格最完美地诠释了这句格言。对于前者,卡夫卡有一句精妙的评语:“她用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的东西。”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在多次精神崩溃后最终走入了家附近的欧塞河,令人唏嘘不已。
恰恰相反,同为女性作家的桑塔格却在一次又一次命运的侵袭中愈战愈勇——26岁离婚(只身抚养儿子并拒绝资助)、一度一贫如洗(只有70美元闯荡纽约文化圈)、诊断出乳腺癌四期(做乳房切除手术)等种种不幸都无法击倒她。晚年,她甚至主动离开舒适圈,走出了伍尔夫所要求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在文明、战火与废墟中观察和思考这个世界——20世纪下半叶每个重要的历史和思辨现场她都不曾缺席。纵观一生,桑塔格在虚构创作与评论性写作之间自如切换,创造出一种格言体式的独特文风,成为继尼采、本雅明、罗兰·巴特之后最重要的随笔大师之一。

苏珊·桑塔格
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知识分子可能沦为“检索机器”的时代(历史学家许倬云感叹“现在的知识分子是网络知识分子,是检索机器,不是思考者”),苏珊·桑塔格凭借深邃的独立思考、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学识,为现代知识分子树立了志业与良心的双重典范。同时,她的文章和足迹横跨文学、电影、音乐、舞台剧、波普艺术、亚文化等,这让她成为世所罕见的“‘文艺复兴式全才’的现代版本”。所有这一切,都让桑塔格本人以及她丰厚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在她逝世20周年后的今天显得更为灿烂耀眼。
疾病
疾病不止生理和医学范畴,伍尔夫或许是最早意识到这一事实的作家之一。她曾这样哀叹:“再不起眼的女学生坠入爱河时,都有莎士比亚或济慈为她倾诉衷肠;但若要一个患者向医生描述他的大脑中的疼痛,语言立即干瘪无力。没有任何现成的词句供他使用,他被迫自己去创造新词,一手拿着疼痛,另一手拿着声音。”较之伍尔夫,桑塔格在这一核心问题上显然走得更远——她敏锐地意识到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被污名化,用桑塔格的话说即“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变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最终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
这一敏锐的感受力与桑塔格的人生际遇密不可分。1975年,42岁的苏珊·桑塔格被诊断为乳腺癌四期。彼时,西方社会对癌症的认知有限,除了对病痛和死亡的恐惧,还有隐形的社会偏见笼罩下的耻感。面对从天而降的凶险疾病,一向冷静理性的桑塔格也陷入了慌乱与震惊。她满腹狐疑地问医生:“是不是我的生活方式不当导致的?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她甚至怀疑是因为自己的性生活太少了。桑塔格之所以会产生如此联想,是因为当时的癌症被普遍认为是心情压抑或身心受到重创所致,自责、愧疚等来自精神和道德上的压力在无形之中紧紧地缠绕着她。所幸的是,冷静之后的桑塔格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也开启了她后半生异常精彩的战斗人生。
桑塔格发现历史上被困在“疾病王国”中的作家不在少数,比如生前饱受结核病折磨的卡夫卡。在1917年10月致好友马克斯·布洛德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已)逐渐认识到结核病……并不是一种特别的病,或者不是一种应该享有一个特殊名称的病,而不过是强劲的死亡细菌……”桑塔格敏锐地意识到,许多时候种种将疾病神秘化的社会偏见比疾病本身更为恐怖。桑塔格勇敢地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并采用在当时极具挑战性的疗法——她坚定地要求医生为她进行长达两年半的电疗。这一时期,她游走于数家肿瘤医院,与众多同病相怜的病友结识。桑塔格逐渐意识到,世界中充满了隐喻和被遮蔽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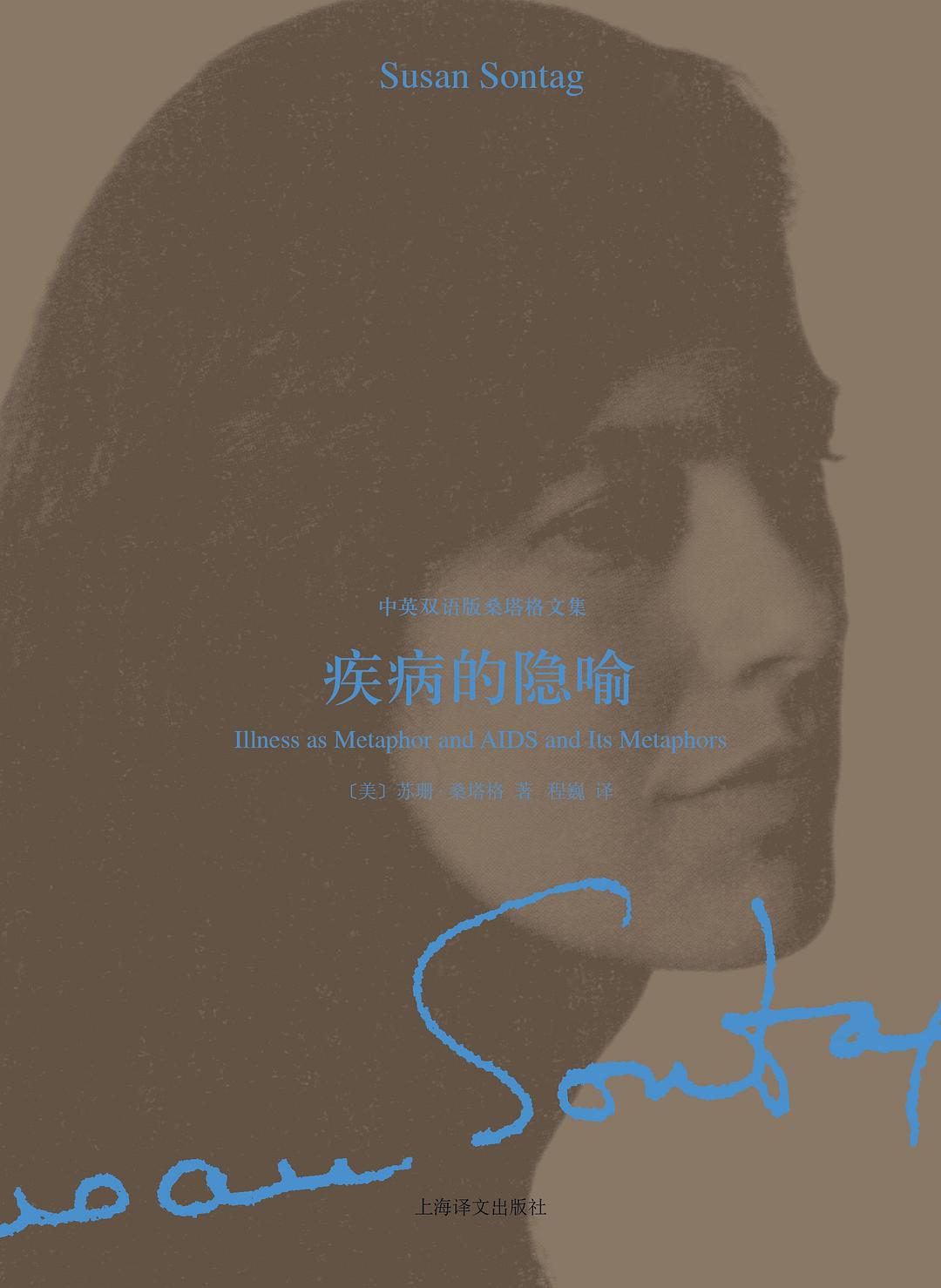
《疾病的隐喻》
残酷的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桑塔格开始写作《疾病的隐喻》:“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在她看来,那些具有反智色彩的虔信态度以及廉价的怜悯,使患者除了遭受疾病的痛苦,还承受着精神上的压力。在她身上,身体上的反抗与思想上的精进几乎同步发生。长达两年半的治疗后,桑塔格虽然永远地失去了一只乳房,却奇迹般地战胜了癌症,并带着新作《疾病的隐喻》(1978),成功地重返人间。在这部在西方社会引发巨大反响的作品中,桑塔格祭出了这个如今依然发人深省的著名观点:
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者抵制隐喻性思考。
毫无疑问,这场近乎绝症的疾病及其反抗与反思成了桑塔格一生的重大转折点。在《纽约时报》1978年那场几乎令人眩晕的访谈中,桑塔格这样回应:“它给我的人生添加了一种凶猛的强度……它真正地让你认清了事情的轻重缓急……我认为同生命和死亡保持联系,是件好事。当你积极而自觉地面对它们的时候,你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能量。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种尽最大可能去关注的方式。”但命运的侵袭并未结束。1998年7月,65岁的桑塔格被诊断出宫颈癌。她毅然做了彻底的子宫切除手术,并进行了漫长的放化疗医治。正如她在23年前坚信的那样,她可以战胜概率。
与此同时,桑塔格出于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意愿再次投身写作——她甚至认为自己才刚开始真正写作,而最好的作品尚未到来。在某种意义上,她将作品视为自己必然死亡的使命的延续。2000年3月,67岁的桑塔格在采访时宣称:“我有一个完全崭新的人生。一天只有24小时,但我试着以48小时来对待它。”桑塔格一直坚持谈话、阅读、看电影,她甚至开始学习钢琴,这是她母亲在小时候禁止她做的。戴维·里夫在桑塔格死后出版的散文集《同时》(2007)的序言中描述,他的母亲属于这样一类作家,“他们在面对死亡的必然性时,以幻想他们的作品会比他们活得更久……来安慰自己”。显然,桑塔格做到了。
坎普
据我所知,很多中国读者是因为《疾病的隐喻》或《论摄影》(1977)这两本经典熟悉和走近苏珊·桑塔格的。但事实上,当年让桑塔格在西方社会一举成名并引发轰动的,乃是她1964年秋天发表在《党派评论》上的一篇文章,题为《坎普札记》。文章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开头:“世界上有很多事从来没有被命名,还有很多事虽然被命名了,但是从来没有被描述过。”桑塔格辩论说,“坎普”(Camp)是一种专注于技巧的辨识力,它巧妙地认定风格比内容更有价值。在此,桑塔格成功地定义了一种趋势,而且她那漫不经心、稳操胜券的口吻与谈论的主题形成了完美的搭配,这让该文迅速引发了巨大的热议与反响。
“坎普”一词源于法语se camper(摆姿态)。事实上,桑塔格并没有发明“坎普”这个词,而是给了它新的生命。她断言,坎普是一种“感受力”。为了在字里行间把握这种独特的感受力,桑塔格认为应该采取更加灵巧的方式,于是她极富原创性地祭出58条编了号的笔记,由此联缀而成的这篇独特之作被题献给她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坎普大师——奥斯卡·王尔德。很多苏珊的粉丝都知道,她将王尔德的警句之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要么自己成为一件艺术品,要么就在身上穿戴一件艺术品”。在所有这些思维敏锐、视野宽广甚至有些卖弄学识的文字背后,藏着桑塔格心中一个隐秘的观念:
在高级文化(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的)及其伟大人物享有的庄严名望之侧,我们也应当给另外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感受力留出它们应得的位置。
用更加通俗的语言来说,桑塔格要为流行文化争取一席之地。在她看来,精英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她试着用自己敏锐的感受力去建立一座桥梁,将整个世界统一起来。在这个不再割裂的世界中,坎普就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将世界看作一个美学现象”的存在方式,坎普的美学特质可以赋予任何一件具有相关属性的物品,“电影、家具、服装、流行歌曲、小说、人、建筑,都可能是坎普式的……”在第四条札记,即“以下随意列举的一些范例,属于坎普经典之作”中,她像扔手榴弹似的掷出了一长串令人感官眩晕的冲击弹:
《祖雷卡·多布逊》
蒂凡尼的灯具
斯戈皮顿公司出产的电影
洛杉矶的布朗·德比旅馆
《探询》,标题以及报道
奥勃雷·比尔兹利的绘画
《天鹅湖》
贝里尼的歌剧
维斯康蒂导演的《莎乐美》和《可惜,她是一个婊子》
世纪之交的某些美术明信片
肖德萨克的《金刚》
古巴通俗歌手拉·鲁普
林恩·沃德的木版印刻的小说《上帝之子》
弗莱希·戈登的老式连环画
二十年代的女装(皮毛披肩,饰以流苏和珠子的上装)
罗纳德·菲班克和艾维·康普顿贝内特的小说
只供男子观看的不激发欲望的色情电影
如今,我们可以将这种行文风格视为典型的“桑塔格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她将无数离散的事物串联起来的惊人能力。这篇流行文化的宣言取得了巨大成功,著名的《时代》杂志以《趣味》为题转载了其中的几段,将苏珊塑造为“不可小觑的人物”。1965年的整个冬季,纽约各大沙龙最中意的游戏就是分门别类,什么是坎普的,什么不是。一次晚会上,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注意到了这位耀眼动人的知识界新星,决定请她为自己的默片“试镜”。桑塔格同意了,她至少做了两次模特。她试图展现出某些独特的个性与气质,尽管有时不够自然。她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会精通这门艺术,精通于掌控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写作方式,还有自己的情感生活。
无论如何,写作成为她心目中理想人生的核心——她想要过一种严肃的人生。有趣的是,这个严肃人生的重要开端正是这篇满是自嘲与反讽,甚至为流行文化辩护的“坎普”札记。从被桑塔格视为源头的充满戏剧性和明暗对比的卡拉瓦乔,到如今被誉为“时尚界奥斯卡”的Met Gala(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那种兼具天真与复杂、质朴与技巧的坎普之风无处不在。可以说,在那个流行文化迅速崛起的时代,桑塔格取得了一个年轻作家所能获得的一切成功,但她的伟大之处在于,她永远不会满足于眼前的成功,而是不断在尝试新的渴望与新的挑战,永不停歇。
萨拉热窝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如果没有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萨拉热窝事件”,这座毫不起眼的城市注定将默默无闻。尽管1992年3月爆发的波黑战争引发了一场现代战争史上时间最长的都市包围战——萨拉热窝围城战,但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如今已几乎被世人遗忘。然而,桑塔格为这座伤痛之城所做的一切永远无法让人忘记。这位极为早慧的女性自小就思考如何反对不公正的问题:自从她读过《悲惨世界》,自从她在圣莫尼卡的一家书店里第一次看到大屠杀的照片开始,便一直思索这个问题。萨拉热窝位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交汇处,这也是桑塔格一生追求的兴趣交汇的地方:艺术家的政治角色和社会责任,试图将审美与政治结合起来。
先期抵达波斯尼亚的是戴维·里夫,继承了母亲抗争精神的戴维隐隐地相信文明世界是存在的,自己有责任告诉这个文明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后来,戴维问后来创立萨拉热窝电影节的米罗·普里瓦特拉,是否需要他下次带东西或人过来。对方说:“最适合来这里了解情况的人之一肯定是苏珊·桑塔格。”几周后,戴维出现在米罗家门前,同行的还有桑塔格。戴维并没有说桑塔格是自己的母亲。不同于那些喜欢作秀的名人或政客,说几句漂亮话,或留下几张表现同情心的照片,桑塔格早就在《论摄影》中给出过警告:战争照片会变成“人们业已熟悉的暴行展览,而且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不断重演”。除了食物、钱、水和香烟,她在思考为这座战火中的城市带去什么?
最终,桑塔格与国际戏剧节的负责人帕索维奇讨论起要制作一部戏剧。在她心目中,萨拉热窝人在战火中失去了“生而为人”的生存尊严——当衣食住行都成了一项极为冒险的挑战,文化和艺术,也许能够在另一个时空里给予他们高贵的生命。对此,她写道:“文化,是人类尊严的一种表达”。苏珊先后考虑了阿尔弗雷德·贾里的《愚比王》,以及贝克特的《哦,美好的日子》,直到某日帕索维奇的一句“但是苏珊,在萨拉热窝,我们在等待着”,她眼前一亮。1953年,阿兰·罗伯·格里耶在距离《等待戈多》首演不到一个月时写道:“没有哪部戏运用的戏剧手段比这部更贫瘠了。”他指的是贝克特选择的戏剧手段:布景由稀疏的树和垃圾桶组成;语言极其简单;一共五个角色,其中一个看不见,一个不能说话,等待着一直也没有等来的救赎和高潮。
这些当年艺术上的隐喻,在40年后的萨拉热窝变成了残酷的日常现实。1993年那个炎热、饥饿的夏天,桑塔格和演员们每天工作10个小时,整部戏的制作是在没有电(只能在烛光中进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戏服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所用的布景也不过是联合国发放的塑料布——用来替代狙击手打碎的窗玻璃。《等待戈多》对现场观众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受到了广泛的国际关注,但它无法救回骑车的男孩的命,也没有带来军事干预。但是,桑塔格找到了一种方式,可以将她自己能够奉献的东西都奉献出来。

位于波斯尼亚民族剧院前的苏珊·桑塔格广场
1995年下半年,波斯尼亚战争交战各方签署了《代顿协议》,在那之前苏珊又回到波斯尼亚7次。协议签署之后,萨拉热窝长达1425天的围困终于结束了。在这三年多时间中,苏珊的生活变得与波斯尼亚密不可分,萨拉热窝成为桑塔格生命中一个难以磨灭的关键词。如果被称作现代艺术家——现代人——的条件之一是:他或她知道戈多是不会出现的,那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不被需要,不会有所作为。桑塔格决心要有所作为,这让她变得与众不同。她去世后,波斯尼亚民族剧院前的广场被命名为苏珊·桑塔格广场——这是萨拉热窝所能授予的最高奖项,桑塔格完全配得上。桑塔格留下的文字将与这座广场一样不朽:
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